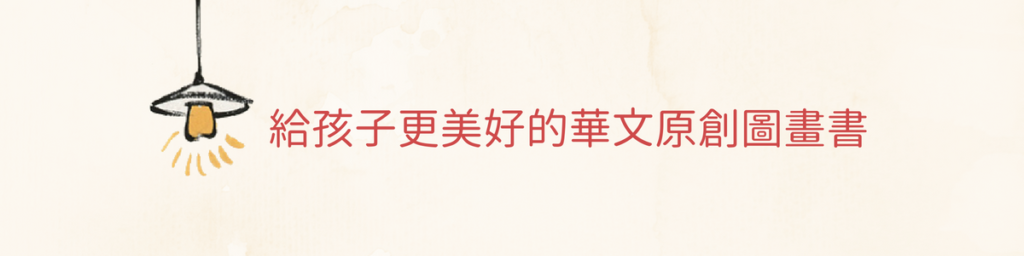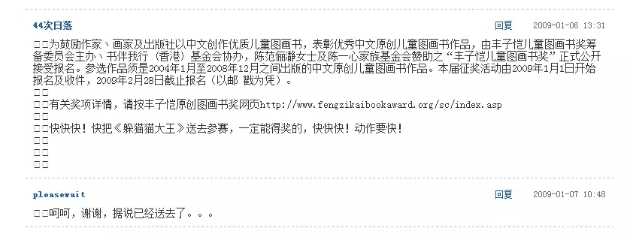News & Events
書獎於2008年成立,跨地域推廣華語圖畫書已十個年頭,舉辦了五屆頒獎典禮並評選了32本優秀圖畫書。為此,我們向創作者、推廣人、研究者及學者發出邀請,將他們與豐子愷兒童圖畫書獎及原創圖畫書一起成長的經驗分享給大家。
那麼遠,這麼近
我和「豐子愷兒童圖畫書獎」的十年
—孫玉虎—
2014年,徐燦和中西文紀子
大概是2014年,有人找到我,說要做一個中日韓三國的繪本項目,文字由我來操刀,畫家嘛——他們告訴我一個名字:徐燦。咦,好耳熟的名字!我隱約記得在第三屆豐子愷兒童圖畫書獎的頒獎活動期間見過這個人。於是我找出躺在抽屜深處的名片夾,一張張飛快地翻起來,終於找到了——的確是同一個「徐燦」,某出版社美編。
當時的頒獎活動,這個叫“徐燦”的人就坐在我旁邊,她正和她的一個女同事討論著主辦方發的圖畫書。看到她手裡拿的是湯姆牛的《下雨了! 》,在一旁沉默良久的我終於忍不住問她:「請問,這本書到底好在哪裡?」她略帶嫌棄又一臉熱情地說:「我給你講一遍哈!」於是她快速翻動書頁,用一種「上課鈴快響了時間來不及了」的語速,把《下雨了! 》從頭到尾給我講了一遍。每頁保守估計用時5秒鐘。
經她這麼一講,我還真的領會了湯姆牛的創意,從此愛上了這本書。但徐燦到底長什麼樣,我卻有點想不起來了,可能當時我正全情投入在她繪聲繪色的講演中,無暇顧及其他。我只記得我們交換了名片,我告訴她,我是一個寫故事的人。所以,我對徐燦能否認出我來表示嚴重懷疑。
為了那個「三國」繪本,出版方組了一個飯局。遠遠地,徐燦走過來了,面無表情。我說我是孫玉虎,我們在豐子愷獎的活動中見過。她說我記得你。我表示驚訝。她說,我的圖像(人臉?)記憶能力很強。於是我對她有了那麼一丟丟崇拜。然後她拿出她畫的《老鼠嫁女》,借鑒了皮影戲的造型和色彩,於是我對她的崇拜又增加了幾分。
當時那個飯局上還有中西文紀子,徐燦就是經她介紹給出版方的。我那時候剛闖入圖畫書世界也就兩年,不太懂這些人是什麼來頭。我只記得中西小姐有一張像福原愛一樣的娃娃臉,我們在路邊等車的時候,她會獨自走到一邊安靜地抽完一支女士香煙。我當時在心裡默默地想,這個女人好酷啊。後來我才知道,中西小姐就是《荷花鎮的早市》和《迷戲》的編輯。


哦,那個「三國」繪本的設定是這樣的:一個小男孩,分別到中、日、韓三國旅行,從而串起三個國家的風土人情。第一個故事發生在北京,由我來寫文字。然後日本和韓國再接龍下去。出版方告訴我,這是外交部的項目,目的是為了促進中日韓三國的睦鄰友好關係。等書出版之後,會邀請各國的首腦來推薦。說到這裡,出版方可能自己也覺得請到各國首腦不是很現實,於是馬上改口為各國首腦的夫人(韓國除外)。他說:「中國請彭麗媛,韓國請朴槿惠,日本請……哎,就請日本天皇的夫人吧。——想想看,你是中國版的文字作者,到時候你就一戰成名啦!」
聽著這些話,我內心冒出一萬個“excuse me”,尷尬又不失禮貌地微笑著。雖然這真的是外交部托辦的一個項目。
為了這個項目,我、徐燦和中西小姐,在某個週末一口氣遊覽了故宮、中山公園、前門大柵欄。就是那一次,中西小姐帶我們去了美術館後街亮果廠胡同一家名叫“老宅院”的烤鴨店。後來“故宮—中山公園—老宅院”成了我領外地客人遊覽北京的經典路線,因為逛完剛好可以趕上吃午飯。那天下午我們去了大柵欄,那是我第一次去大柵欄,我們每人買了一支吳裕泰的抹茶甜筒,看了布鞋店、絲綢店、茶葉店、醬菜店、古玩店、文房四寶店,還看了在馬路中央往往返返的觀光小火車。
可惜,不久之後,中日韓三國的關係越發緊張起來,「三國」繪本被叫停了。我加了中西小姐的微信,卻再也沒有說過一句話,因為她沒有朋友圈;我倒是經常給徐燦點點贊,證明我還活在她的朋友圈裡。我們誰也沒有再提起那個關於「三國」繪本的偉大構想。
三年之後,我在另一本圖畫書的版權頁上看到了“中西文紀子”這個名字,那本叫《盤中餐》的書後來拿到了第五屆豐子愷兒童圖畫書獎的首獎,中西小姐是特約顧問。
後來我認識了一些朋友,當我們談到圖畫書的時候,無意中發現我們都曾參加過2013年那次豐子愷獎的頒獎活動。 2013年,那是第三屆。有時候我會想,為什麼偏偏是第三屆,而不是第一屆或者第二屆。
我本人是2012年開始走進圖畫書世界的,我在很多場合都說過我跟圖畫書的相遇源於一次跟朋友的打賭,是偶然。實際上,也是必然。在此之前,豐子愷獎已經評選了兩屆。我至少看過或者聽說過《團圓》《一園青菜成了精》《躲貓貓大王》。
尤其是《躲貓貓大王》,可能很多人是因為它得了豐子愷獎才知道的這本書,我不是。我很早就知道《躲貓貓大王》了,它的前身叫《小勇》。而早在2004年,我就通過文字認識了它的作者張曉玲。 《小勇》只是她很小很小的一個故事,她真正的才華在她的那些數量稀少的少年小說裡,比如《海嘯》,比如《白鞋子》,比如《斐濟的陽光》。我永遠記得《海嘯》的結尾,合影上的少女站在最右邊,但眼睛仍在往右看,笑著,好像那里站著一個人;我永遠記得《白鞋子》的結尾,女孩決定用剩下的那隻白皮鞋做花盆,裡面種上蒲公英,當蒲公英的種子四散飄飛,一定很好看;我還記得在《斐濟的陽光》裡,女孩和她的小姨,兩人同蓋一條薄絨毯坐在卡車後面的車斗裡,星光灑在毯子上。
所以,當我根本不知道什麼是圖畫書的時候,我無意中看到了第一屆豐子愷兒童圖畫書獎的徵獎啟事,就興沖沖地跑到天涯博客上對張曉玲說,拿《躲貓貓大王》去參加比賽吧,你一定能贏!那是我,一個張曉玲的忠實讀者,基於讀了《小勇》之後做出的最莊嚴的判斷。
△ 2009年的天涯帖子,有圖有真相
後來,《躲貓貓大王》真的贏了,它成為豐子愷獎評選以來唯一的評審推薦文字創作獎。那應該就是我對豐子愷獎最初的記憶,那一年是2009年。
此後四五年間,我都離豐子愷獎很遠很遠,作為一個寫小說的人,從來沒想過自己會跟豐子愷獎有什麼交集,直到2013年。
那一年我的運氣格外好,在同一屆信誼圖畫書獎中拿了兩個文字創作組佳作獎。這也是為什麼後來那個「三國」繪本的出版方會找我來寫腳本的原因。有了得獎的鼓勵,我對圖畫書的熱情更加高漲,自然關注到了那一年豐子愷獎頒獎的消息。
實際上,第二屆頒獎的時候我就注意到了。那是2011年,正是微博最火的時候,豐子愷獎在微博上搞了一個10進5的有獎競猜,我隨便瞄了一眼,看到有人負氣似的說:「我不知道誰會得獎,但我知道我不希望誰得獎。」但後來頒獎啊什麼的我從來沒想過要去圍觀,雖然地點就在北京。
2013年,第三屆和幾米
那為什麼偏偏2013年我就從北京吭哧吭哧跑到南京去參加豐子愷獎的活動了呢?我想除了我也開始寫圖畫書故事了,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那一年豐子愷獎演講嘉賓請的是幾米。
幾米對我們八零後這代人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如果說我們小時候也有過圖畫書的啟蒙,那麼就是來自幾米的那些所謂的「成人繪本」。在學生時代,我們會把幾米的繪本作為生日禮物送給好朋友。我記得自己「斥巨資」買的第一本幾米繪本是《月亮忘記了》。想想吧,那是2000年初,一個蘇北小縣城裡的窮學生,居然捨得花二三十塊錢去買一本只有寥寥幾個字的繪本,簡直了!所以,當得知我有可能見到活的幾米,可以親耳聆聽他的演講時,我毫不猶豫地買了票,坐上了南下的火車。
那一次,幾米分享了他創作兒童圖畫書的心得,可謂“乾貨滿滿”。其實,幾米接受國外編輯的約稿,開始創作兒童圖畫書的時候,他已經大紅大紫。可編輯還是會一遍又一遍地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見,為了說服幾米,編輯還會拍編輯部的視頻發給幾米,為他加油打氣。這樣一來,幾米被感動了,只好乖乖地去改稿。那是我第一次見到創作一本圖畫書是多麼的繁瑣和復雜,此後我看過很多關於原創圖畫書的創作分享,無論多麼反復和曲折,對我的震撼,都不及幾米分享的那一次。而且幾米是用一種幽默的方式來講的,格外吸引人。
在這裡,我必須莊嚴地告訴大家那幾本圖畫書的名字:《不睡覺世界冠軍》《吃掉黑暗的怪獸》《乖乖小惡魔》。
2013年,第三屆和安東尼·布朗
2013年那屆豐子愷獎還請了另外一位演講嘉賓:安東尼·布朗。
我對他的感情很複雜,像《我爸爸》《我媽媽》這類清清爽爽的作品我能夠知道它們的好,可是面對諸如《隧道》《大猩猩》之類的作品我就無感了。記得那次我坐在觀眾席上,看著台上的安東尼·布朗講他在作品裡藏了怎樣的玄機,我整個人感到非常煩躁。我從來不認為一個需要另加解釋的作品是好作品,那隻不過是給評論家們留一個飯碗罷了。
三年之後,我在上海看了安徒生獎50週年插畫展,當我站在安東尼·布朗畫的巨幅大猩猩面前,看著那纖毫畢現的一根根金色毛髮,我忽然被打動了。從那一刻起,我開始放下自己的偏執,試著去理解每一個創作者的良苦用心。
2013年,第三屆和方衛平先生
除了幾米和安東尼·布朗,2013年我還記住了方衛平先生。我永遠記得他作為主持人的開場白:「有一個男人,我愛他愛了很多年……大概2000年左右的時候,我無意中看到他的幾個繪本,大驚,畫得真好啊……這個男人,就是幾米……」
2012年「五一」,我去浙師大找還在讀書的兒童文學作家吳洲星玩,她帶我去那棟著名的紅樓拜訪方衛平教授。她告訴我,方老師辦公室的窗戶如果是開著的,表示他在,可以拜訪;如果是關著的,表示他不在或者不願意被打擾。那天我很幸運,窗戶是開著的。
2013年見到的方衛平跟我2012年見到的方衛平完全是兩個人,2012年的方衛平有點嚴肅,2013年的方衛平則幽默風趣。 「他們」就像一個人的兩個面向,在我心裡越發生動起來。我不知道他還記不記得曾經在紅樓跟他聊過一個小時的年輕人,只是遠遠地看著他,在台上,在人群中間,哪怕上前去打個招呼都不好意思。
2015年,第四屆和方衛平先生
轉眼到了2015年,我跟方老師因為工作關係有了一點交集。那一年評的是第四屆豐子愷獎,有一次我們通電話,方老師得知我報名了在浙師大舉辦的豐子愷獎活動,問我住的地方訂好了沒。我說沒有,我說等我到了之後在學校附近訂個賓館就好。方老師說如果你不嫌棄我們可以幫你在學校的國際交流中心訂一個房間,去活動會場也方便些。我受寵若驚,不知說什麼好,唯有連聲感謝。
那一回,我跟蒲蒲蘭的編輯們坐的是同一趟火車,抵達金華已經很晚了,方老師專門請學生和校車來火車站接我們。到了國際交流中心,蒲蒲蘭的編輯們登記入住了,我在前台等著方老師給我安排房間。可是——房間——沒有了!我硬著頭皮給方老師發了短信(打死我也不敢相信我會直接打電話去問),旁敲側擊地問了一下房間的事情。方老師了解了一下情況,最後讓我到他的房間去住。是的,到——他——的——房——間——去——住。
我就這樣謎一般地住到了方老師的房間,是個雙人標間。雖然時間已經很晚了,但還是有很多方老師已經工作了的學生這次回母校參加活動,他們三三兩兩地來到方老師的房間,或帶來家鄉的特產,或帶來對老師的問候,總之,很熱鬧。他們看到我,很好奇,咦,日落大叔也在哦?我不知道怎麼向他們解釋我的存在,只好尷尬又不失禮貌地撓頭微笑。
實際上,那天晚上是第四屆豐子愷兒童圖畫書獎頒獎典禮的前夜,是最忙最亂的時候,而方老師作為組織者,是最最操心的那一個。儘管如此,我們還是聊到夜裡一兩點。就是那一晚,方老師給我講了洛貝爾的《驚喜》和《等信》,而我居然給他復述了一遍我寫的一個故事。最後聊著聊著,我們的聲音終於漸漸微弱下去。
等我醒來的時候,已經早上六點多,那時候方老師已經坐在床上寫著什麼。我問他在幹嗎,他說在寫評審報告。啊?馬上就要頒獎了,他的評審報告還沒寫嗎?我居然還不知趣地拉著他開了一晚上「臥談會」。頓時,我的心裡充滿了自責。
等到方老師去洗漱的時候,我偷偷地看過那張寫滿字的紙。字蹟有些潦草,大多數都認識,也有幾個字不認識。只是大致列了個提綱,並沒有展開寫。看著那些陌生的字跡,我忽然想起我小學三年級的時候有個數學老師租住在我們家屬院裡,他喜歡騎腳踏車上班,每次在路上遇到我,都會載我一起去學校。我坐在他的後車座上既緊張又興奮,總是把車座抓得牢牢的。同學們知道這件事,老愛向我打聽數學老師的小秘密。其實我並不知道什麼小秘密,我從沒去過數學老師租住的那戶人家,於是我就開始編造一些「小秘密」講給同學們聽。那時候我就在想,做老師家的孩子真好啊。那天早晨,看著方老師的字跡,那種熟悉的感覺又回到我的身上。/p>
頒獎典禮開始了,方老師作為評審主席發表評審報告。我坐在台下比任何人都聽得仔細,在心裡比對著哪些觀點是紙上寫的,哪些觀點是臨時加進去的。活動期間,我還負責幫方老師看守那隻黑色的公文包,跟他一起出入餐廳,像一個忠心耿耿的助理。我還以為這是你的學生呢。有人這樣對方老師說。
事實上,對待每一個與會者,方老師都在目力所及處做到無微不至。我不過是想在自己的能力範圍內,稍稍幫他一些罷了。正因如此,第四屆豐子愷獎的頒獎活動成為我記憶裡最溫暖的一屆,沒有之一。
2019年,期待第六屆老友聚
轉眼到了第五屆,我因為在北京參加另一個頒獎活動而與我期待已久的演講嘉賓大衛·威斯納完美錯過。其實北京那個頒獎活動,方老師也參加了,但他活動一結束就飛往了合肥。我是沒有他那麼精力充沛的,我現在只等著下一屆豐子愷獎活動趕快開始,也好讓我跟圖畫書發燒友們多一個相聚的理由。
在這等待的時間裡,應鄭先子老師之邀,胡亂記錄下這些跟豐子愷獎有關的碎片,以對抗時間的流逝。
掐指一算,恰巧十年了。
我知道我的作品離豐子愷兒童圖畫書獎還很遠,但因為這十年間遇見的那些人那些事,我又覺得自己離豐子愷獎是這麼近。■
(本文中的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 本文作者 | 孫玉虎
網名「四十四次日落」。 2003年開始發表作品。曾獲第十屆全國優秀兒童文學獎、《國語日報》牧笛獎首獎、青銅葵花圖畫書獎銀葵花獎、香港青年文學獎、冰心兒童文學新作獎、《兒童文學》金近獎等。 2014年被評為鳳凰傳媒·中國好編輯。近年來致力於圖畫書的研究與創作,在第四屆、第五屆信誼圖畫書獎中共獲得三項文字創作獎。已出版兒童小說集《我中了一槍》、橋樑書《遇見空空如也》、圖畫書《其實我是一條魚》《那隻打呼嚕的獅子》《那條打噴嚏的龍》等。曾任《兒童文學》小說編輯七年,現居杭州。